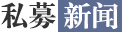导读:“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一直是王晓东的座右铭。他身上有很多标签: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40岁的时候放弃美国的高薪职位毅然回国;41岁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内地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同时,他还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药研发企业百济神州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创办公司、研发新药的初衷就是让国内癌症患者可以用上全世界最好的国产新药。
作为百济神州在中国唯一的全程投资人,高瓴参与和支持了百济神州从成立以来的每一轮融资。制药行业回报周期长,投入巨大,但高瓴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寻求短期回报,希望在特定领域做深、做精,而这也与王晓东的科研精神不谋而合。放眼十年、二十年,高瓴愿意和百济神州一起齐头并进,做时间的朋友。

中科院外籍院士
百济神州的创办者
41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轮值主席
王晓东,这位在生命科学领域走在国际前沿的科学家,有着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总给人以谦谦君子的感觉,然而他的骨子里,却充满了“冒险”精神。
他的研究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肿瘤治疗药物。
他创造性地运用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揭示了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凋亡通路,首次发现并阐明了线粒体作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机理,把细胞凋亡由线粒体的上游调节和下游执行通路连接起来;并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对于线粒体提供能量和代谢场所的传统认识,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认为细胞内主要的细胞器及其功能已被发现的最大颠覆。
这不仅是细胞生物学中一个概念性的转变,对进化、发育等基本生命活动的认识,以及重大疾病如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和治疗都有重大意义。当今对哺乳类细胞凋亡生化通路的认识大多数来自王晓东的实验室。
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述一下王晓东的传奇经历。
“我做事想事,有点不拘一格”

1980年参加高考时,因为“不拘一格”,不喜欢死记硬背,王晓东的有些科目分数并不高。
当时英语还不算高考的主要科目,王晓东却在整个考区得分最高。虽然只能折算30%,貌似有点吃亏,可是王晓东说“我喜欢英语,我不在乎”。
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后,王晓东学得很认真,也追求过高分——大学一、二年级时,所有的专业课都在90分以上。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王晓东很“受刺激”的事情——他发现考高分原来是有“捷径”的。
在临近期末考试老师答疑的时候,有同学去套题,并从老师回答的蛛丝马迹中揣测考试会考什么,不考什么。结果,平时学习非常勤奋的同学,可能分数还没有走捷径的同学分数高。
“这个标准不对,不能反映真正的水平。这样的考试没有意义。”王晓东说。
他觉得分数没有那么重要了。到了大三,王晓东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读英文原版教科书上。这次他有了个新的目标——CUSBEA。
当时在中美两国留学渠道还不通畅的情况下,美籍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了这个项目,旨在选拔优秀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CUSBEA始自1981年,于1989年结束,共有422名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CUSBEA用的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考试试卷,考试内容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所以试卷用的是英文。王晓东很轻松地考过了,秘籍就是“原版的英文教科书”。
那是77级的师兄师姐在参加第一年的CUSBEA考试时复印的。现在看来颇有些传奇的味道:据说全北京当时只有6本教科书。北师大77级学子在晚上,找到有复印机的地方,复印了一个晚上。
这本书成了“宝典”在生物系流传。大三的时候,“宝典”传到了王晓东手里。那个假期,他背着一书包的“宝典”回了河南老家,看了一个假期,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真正做科学的精髓:无所畏惧。”

1991年,在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王晓东来到了同校的分子遗传系,跟从198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从事博士后研究。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选择王晓东的过程颇有戏剧性:他们给王晓东的博士导师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是个好人吗?
然后,王晓东就得到了这个博士后的资格。
在这里,王晓东真正学到了做科学的精髓:无所畏惧。
王晓东说:
“你现在最想、最应该、最能做的是什么?绝大多数选择做自己能做的。而这两位老师只问:这是不是应该做的,从来不问能不能做。在他们看来,如果应该做,就做好了。”
这种精神感染着王晓东。也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他在当今最前沿学科的研究渐入佳境。从1995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室后,王晓东的论文成果到目前已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4.9万次。
在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当时他所在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可王晓东却说,“以前做的事情应该尽快忘掉,永远往前看。”在他看来,你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是不是真正在科学前沿做事,不在于以前做了什么,而是现在还能做什么。
细胞凋亡

1995年王晓东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他已经决定将寻找凋亡通路中的蛋白定为实验室未来的研究方向。
凋亡体(apoptosome)的发现
王晓东的实验室清晰地描绘了这些蛋白在凋亡中相互作用的情景:细胞收到凋亡信号刺激后,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中释放到细胞质,它与Apaf-1作用增进了与ATP/dATP的结合,与ATP/dATP的结合使Apaf-1蛋白CARD结构域相互作用多聚化,形成的含有7轴对称的蛋白和核苷酸的复合体被命名为凋亡体。凋亡体中的Apaf-1结构发生改变,招募caspase 9并导致caspase 9被剪切成两段,从而被激活。激活了的caspase 9进一步地剪切caspase 3。
王晓东的以上发现在生物界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很多科学家参与到细胞凋亡的领域中来,竞争开始变得非常激烈,而凋亡的研究也在飞速发展。
凋亡体上游与下游执行蛋白的发现
顺流而下,caspase 3的激活导致了细胞核DNA被剪切成核小体DNA大小的片断,那么中间的执行者是什么蛋白呢?通过生化实验以及与华人施一公实验室解晶体结构的合作研究,王得到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由于该领域激烈竞争,王晓东对Smac以及之前的endonuclease G研究的结果都是和其它科学家的结果同时发表在一个期刊上。王晓东的结果都是用体外重建的方式清晰阐明的,进一步梳理了调亡的线粒体途径。
新的视角,新的起点
以上的重要发现让王晓东获得了荣誉,也使他有能力决定新一轮的研究方向。
例如Smac的N端氨基酸促进调亡的作用有可能用于开发治疗癌症。王晓东与其他人合作,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此外王晓东还将“建立体外检测体系-跟踪纯化活性”的模式用于研究RNAi的机理。
40岁的勇气,很庆幸自己选择回国

施一公说,是王晓东的一句话促成了他的回国决定。不过,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然而如今的王晓东回望当年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在国外,我们就有很多思想上的交流和学术上的合作,回国的选择也有互相之间的鼓励,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时代烙印。”王晓东习惯性地对自己的影响轻描淡写。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回国这条路”,王晓东说,“一方面自己的科研还在继续,而且至少不比在国外差,另一方面,自己可以在科研之外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回国,最清晰的客观效应可能有两个”,王晓东解释,“一个是我们以身作则,表明在中国也能做世界一流的科研,现在年轻人的回国潮已经很明显;第二,这批人真正做到世界前沿以后,一些靠宣传和忽悠的科学家主导中国科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隔路相望的北生所和百济神州

美国留学多年的王晓东,在国内声名鹊起开始于2003年~2004年这两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王晓东先后开始构筑其十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两项事业:北生所和百济神州。
有意思的是,北生所和百济神州都选址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隔路相望,直线距离不到200米,且两个单位共用一个食堂。
建立北生所是中国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之一,其基本的原则是把握时机,以改革试点的方式,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国际一流科学家集体为基础,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建国际一流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所。
北生所的主要任务包括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同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
北生所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而百济神州则更多将精力放在科学研究的转化应用上。自2004年创建开始,百济神州因其创始人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独特地位和其研发实力,一直处在中国创新药研发的第一梯队中,2016年更是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
“打破禁锢原创的所有枷锁,一切以科学作为最终的价值研判”

北生所可以说是所有科研人梦寐以求的天堂,这里有最轻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完全不用为申请项目耗费大量的精力,每个PI每年200万运营经费,配套完善的实验平台完全开放,项目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没有任何所谓职称等级的硬性考核。
“当外面的科研人员绞尽脑汁地发各种论文评职称时,生科所的科学家们正脚踏实地地进行着科学实验。别人都好奇,为什么生科所能发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实际上我们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只是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原创性的东西就会被激发得淋漓尽致。”
有数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研究所独立发表文章257篇,平均SCI为11.19。包括9篇《SCIENCE》、14篇《NATURE》、8篇《CELL》,这在国内外相同领域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

李文辉
2013年,王晓东支持下的“李文辉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在肝脏上的受体,这突破了困扰国际医学领域几十年的难题,为进一步寻求乙肝药物治疗手段提供可能,这是中国原创科研发现。
但是有谁知道,在这项研究进行的五年里,李文辉只发表了一篇小文章。
“要在传统的科研院所,这是无法想象的,大概第一年评职称都过不了。但在生科所,这丝毫没有影响李文辉的项目经费及各项其他保障,大家也没有质疑他的科研能力。”王晓东说。
“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再年轻的科学家也可以比权威做得更好”
有一次,王晓东和一位朋友到食堂吃饭,落座后,朋友诧异“为什么都没人向你行个注目礼”?
王晓东说:“在这没有人把我这个所长当回事儿。”
平等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学生、老师、科研人员和王晓东为一个实验结果展开激烈辩论也是常有的事。
“生科所没有论资排辈,王晓东为这里营造了一种平等对话、自由思辨的科研文化。不是说研究的时间长、获奖多就是权威,任何一个科学家,哪怕是刚进来的不知名的研究员,都可以比所谓的权威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成就。”生科所资深研究员邵峰说。
在2018年《创新中国》纪录片第4集“生命”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所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那个让我荣升为父亲的人

怎样做一个好父亲,是一生的课题。
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往往忙于科研,对家人无暇照顾。
2016年的父亲节,王晓东有感而发,伏案写下一段随想,风趣而动人。
面对高中数学题,科学家父亲也有对儿子崇拜的时候;
那个让自己荣升为父亲的人,打小身体瘦弱,在长跑比赛中总是最后一名却从不放弃,甚至从中悟道“科研真谛”;
父亲由衷欣赏儿子的品质“坚忍不拔”,儿子回赠父亲“他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他”。
以下是原文
那个让我荣升为父亲的人
今天是父亲节。感谢微信朋友圈一早汹涌而来的老照片和文章,真真切切地提醒我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照例起得很早,一人静静地坐在初夏里也已早起的阳光中,脑子里不自觉地想的,全是那个让我荣升为父亲的人。
作为一个科学家,最糟糕的科学实验是那些结果不明确加条件不可控的。两者相加基本就是墨菲定律的实践——只要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而在养孩子这件事儿上,墨菲定律经常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对谁家养出个阳光,出息,有爱心的孩子那是由衷地佩服。
我和儿子第一次相遇
我和儿子第一次相遇,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被错误的事情促成的。我和孩他妈都喜欢体育,研究生期间晚上周末经常在操场跑圈加各种跳跃和力量运动,怀上孩子后也一如既往。结果孩子妈妈在一天晚上锻炼中出血,被赶紧送到急诊室。然后我就在B超屏幕上看到了他——四肢已全,象条鱼似的游来游去。我当时心中充满了惋惜。
然而他在妈妈肚子里竟然顽强地坚持下来了。虽然出生时又一番折腾,但一个健康的男孩还是按时来到了这个世界。虽然出生时只有五磅多一点,但四肢修长,眉目清秀,我也终于升格为一位幸福的父亲。
儿子出生后的几年,在奶瓶,尿布,缺觉和两个博士论文之间交织,具体细节,我如今不管如何努力去想,都是不折不扣的一片空白。看来我的脑区内有强大的自我修饰功能。有印象的就是我们爷俩看了所有迪斯尼的儿童片,有的还是一遍接一遍的看。
崇拜儿子的科学家父亲
有一次看《侏罗纪公园》,看到一群人从被霸王龙破坏的一家星巴克跑到街对面另一家星巴克。哈哈大笑之余,我对儿子说,这星巴克怎么这几年象雨后蘑菇般地冒出来。儿子不屑地回答:这有什么难,你想想他们卖什么?卖兴奋剂!我突然对儿子刮目相看。又问他,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谷歌刚出来几年,做的业务和雅虎一样,为何势头看来要超过雅虎?他想都没想回答说:这两个网站你打开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啥?谷歌就一搜索框;雅虎不知道该看啥,你说谁会在搜索引擎赢?
我对儿子的崇拜就从那时开始了。后来看了他高中的数学题和读书单,基本上只能躲着,怕他问问题。他有一次数学题不会做来问我,我试了半天也做不出。他以后也就再也没问过我。包括后来高中期间在我实验室工作了两个夏天,我也没有怎么指导他。更是一口否决了给他设计一个课题、让他在科学竞赛中拿奖的提议。我口中说我不想让他对科研有不切实际的简单化的印象。但实际上也怕这种粗糙设计的课题被他看穿,我这著名科学家的面子就更没地方放了。
从长跑中悟道“科研真谛”的儿子
但有一点他直到高中毕业,还是跟我差得很远。那就是体育。儿子出生后身体一直瘦弱,协调性差,对运动没有任何兴趣。这在体育为王的美国中学里,是被讥笑的一群。到了高中,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一项运动。他苦着脸来问我:什么运动都不会怎么办?我回答跑会吧。他答:跑不快。我说那就长跑吧。
然后就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四年高中长跑的痛苦的运动生涯。在美国,孩子们的比赛,家长都要观赛,助威和帮忙。长跑队春夏田径赛,秋冬越野赛,几乎每周都有。第一年跑最后一名的从无悬念都是A.Wang。到了第二年初,终于在一次比赛中超过了另一小孩,我们俩高兴得跟拿了冠军似的。然而第二天儿子沮丧地对我说,那个孩子退队了,理由是都被A.Wang追上了,实在没面子再参赛了。然后儿子又成了每次比赛的最后。
到了高中最后一年,教练为他屡败屡战的精神所动,竟任命他为田径队的队长。而队长一般都是运动成绩最好的队员担任的。这下好,在他被加州理工录取后,他们大学田径队的教练专门打电话到家里,邀请他加入大学校队。因为加州理工不以体育见长,多年也没有高中田径队队长级人物加盟,殊不知他这个队长不是因为跑得快,而是因为跑得慢才当上的。结果赶鸭子上架,鬼使神差地代表加州理工参加了四年大学田径比赛。不过这个学校对运动成绩差天然的接受。其男篮曾经创下19年未赢一场的成绩。后来终于“开胡”时,成了当地各大新闻媒体头条。所以儿子仍旧理所当然地跑最后,偶尔某次比赛超过一名,也一定是队友。
加州理工赢一场篮球赛就上头条,显然靠的不是运动实力,而是科研实力。相对于美国多个历史悠久的名校,加州理工建校历史不到百年,学校规模更小,本科生加研究生一共不过两千人左右。然而建校以来,吸引了多不胜数的大师到学校任教和学术交流。从摩尔根到费曼,到设计引力波探测器的索恩(Kip Thorne)。包括以前爱因斯坦和现在的霍金,每年都要到学校住上一段。爱因斯坦住的房间,现在还保持原样,被称作爱因斯坦套房。加州理工培养的学生更是群星璀灿,包括我们熟知的钱学森等多位中国科学家。学校毕业的学生拿诺贝尔奖的比例更是达到了千分之一。
虽然儿子高中学习还不错,不过能上加州理工,我始终怀疑还是他的个人陈述起了主要作用。学校申请有一项讲对科研的看法。他写道:我觉得科研就像长跑。我刚开始跑的时侯经常有两眼发黑想着这是否就是死的感觉。然而坚持一下就又活过来了。科研不应是流星般的绚丽,真正的科研应该是永不放弃的坚持。我窃看后(在他不知情时看的,我想不应叫偷看)拍案叫绝:此子得科研真谛矣。
话虽容易说,不过顺利完成加州理工本科学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课程之难之深可以说有点变态。而儿子又选了化学工程这个课程最多的专业。儿子说第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讲了两小时后,出门时随口说了一句:我刚才讲的是斯坦福大学大一化学课整整一学期的内容。我也曾听一加州理工本科毕业的诺贝尔奖得主亲口讲读本科时累得休学一学期的事。对他们学习的艰苦,我个人也曾亲历过。有一年在UCLA讲演加晚宴。我问他能否从他们学校开车一小时过来参加,他回答晚饭后可以过来。见面后我们找了家咖啡馆落座,我说我的飞机要午夜后才飞,我们今晚可以好好聊聊。然后我顺便问了一句,你今天没事了吧?他回答,我们今天工程数学这门课的作业发下来了。明天交,我今晚不准备睡了。我听完赶紧起身,说赶紧送我去机场,咱们下次再聊。
一生为父子的幸福感悟
一晃我当父亲也二十几年了。在这父亲节里,坐这儿半天,也没想起作为父亲有什么具体的事帮助过儿子,或特别为他操过什么心。爷俩也从未有过情绪化的时刻。儿子高一那年,本地一家报纸作父亲节专版,选了几十对父子、父女,除了把两人四寸照片并排排版以彰显遗传特性外,还背靠背地请你用一句话说出你对父亲(或儿女)最欣赏的品质,然后把这句话印到照片下面。我写下了“坚忍不拔”。而他对我的评价是“他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他”。
其实在对自己人生目标还糊涂的时候,我们父子已为对方看清楚了。
他大三那年,我被加州理工邀请讲演并安排入住爱因斯坦套房。他可能才知道他爸爸的科学做得还行;而他至今坚持长跑,今年半马跑出了88分多的成绩。
从做科学试验的角度养育儿女,真不是一件能拼成功率的事情;做为一个父亲养育儿女,我感激他给我人生带来的精彩。
你所没见过的王晓东

饶毅爱开玩笑,钱学森爱弹钢琴,爱伊斯坦爱拉小提琴,搞科研谁还没点业余爱好。
王晓东在大众眼中都是着装朴素,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然而近几年,每遇新年,北京生科所NIBS的王晓东实验室都有跳舞“大作”问世。
继2016《生科的意义》之后,2018年WangLab推出的黑暗舞蹈《CoinciScience》风格大变,同行们惊呼“做学问和跳舞,都只服晓东一人”,“跳舞界第一流的科学家”。
这就是传奇人物王晓东
人生旅途中经历的颇多转折点
让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却从未改变他对科研的
初心 和 热情
免责声明:本文转载自高瓴资本,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